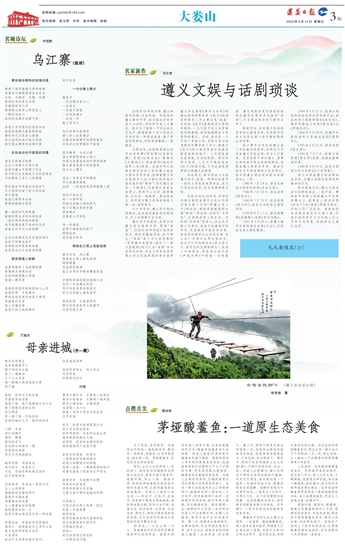石永言
20世纪50年代中期,遵义城惠风和畅,社会和谐。我就读的遵义第四中学,其文娱活动的开展十分活跃,青衿学子里人才辈出。校方为了检验一下学生的文艺水平,便借新城丁字口附近龙井沟内的一间商业食堂,搞了两场售票演出,居然场场爆满,一票难求。
记得当年,这场售票演出的节目有歌舞《荷花舞》《采茶扑蝶》、京剧《打渔杀家》、黄梅戏《夫妻观灯》、歌曲演唱《桂花开放贵人来》等等。这场中学生的商业演出惊动了时任遵义地区行署专员李苏波,他带着警卫员也徐徐步入这个借吃饭的地方临时派作的“剧场”(当时遵义没有一个剧场),与看客们坐在长板凳上,看得开心之时,面带微笑,与大伙一块鼓掌。演出结束后,李苏波与警卫员和退场的人群一起,徐徐离开。
六十多年前,遵义四中的这场演出,生动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,什么时候都不会忘却。
遵义四中的前身,是贵州省遵义省立高级中学,简称“省高”。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,国民党掀起内战,民不聊生。“省高”在丁字口的电影院(即原播声电影院)演出了一部大型歌剧《秋子》,由“省高”音乐老师朱石林、杰生小学音乐老师陈立华以及抗战期间曾经指挥遵义学生演唱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潘名挥老师等执导。《秋子》的演员和剧务人员主要出自“省高”合唱团。《秋子》表现的是日军侵华期间,一名叫秋子的日本军妓的悲惨遭遇,深刻地揭露出日军侵华的暴行。其时,我还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少年,当我从居住的老城来到繁华的丁字口,便看见《秋子》的大型宣传画栏布置在特别显眼的地方。人们围在画栏前观望,且议论纷纷。那时的街头巷尾,人们几乎都在谈论《秋子》的观后感,可见这场歌剧带给山城遵义的影响。
如此观之,新中国成立后的遵义四中,能在一间商业食堂作一场非义务性的售票演出,其文艺活动的传承,是有其赓续意义的。
早在20世纪20年代,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先生任贵州省立第三中学(即遵义老三中)校长时,便在学校提倡学生演“新戏”,即话剧,当时叫“文明戏”,以表现现代人的生活。其时的“文明戏”里的人,女生还不敢上台演出,是鉴于封建意识的作用,但话剧里不能没有女角,甚至有些剧里女生还是主角,怎么办?不得不让男生扮女生。出生于仁怀的韩念龙(原名蔡仁元,曾任过外交部副部长),在老三中就读时,曾在田汉创作的《伊通河畔》中扮演一女性配角。著名戏剧家夏衍曾经在他的长篇回忆录中多次提到“老蔡”,可见韩念龙当时已颇有名声了。
据我所知,当时遵义在话剧里男扮女装演出的,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在红旗小学任教的陈恭让老师等。
由于黄齐生先生在遵义老三中执教时的倡导,话剧这门艺术在遵义开始出现,并为人们接受。及至抗战中西迁遵义、湄潭办学的浙大师生的频频演出,话剧在遵义便普及开来。据浙大校长竺可桢在他的日记里所记,浙大在遵义演出的话剧与戏剧有这么一些:
1940年7月14日,演出反映抗日战争的话剧《自由兄弟》;
1940年7月14日,演出话剧《茶花女》;
1940年7月15日,演出话剧《夜光杯》,剧本为本校学生潘传烈作。
1940年8月17日,演出独舞剧《未婚妻》、戏剧《贺后骂殿》;
1941年5月20日,在遵义播声电影院演出话剧《日出》,目的是为浙江难民募捐;
1944年5月27日,在湘江戏园参加欢送毕业同学游艺会,演出狄青大败侬智高的《昆仑关》、韩世忠取金兀术的《黄天荡》与《罗通扫北》;
1944年5月28日,在播声电影院由外文系演出话剧《悔罪女》;
1945年6月23日,演出话剧《寄生草》;
1945年7月2日,在湘江戏园看《寄生草》话剧,该剧由熊佛西导演。
1946年3月25日,由浙大剧团与外文系演出《万世师表》。
浙江大学在遵义的话剧演出活动,为遵义话剧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。
新中国成立后,遵义文娱活动与话剧的演出,一直不衰。譬如在中华路上的原遵义市京剧院舞台上,就曾经上演过话剧《抓壮丁》与《雷雨》等著名剧目,引起人们广泛关注。虽然这些业余演出者至今大都亡故,但他们留给历史文化名城人们心中的艺术形象,却始终让人难以忘怀。